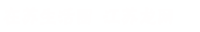зҪ—зҰҸе…ҙйЎҝдәҶйЎҝ пјҢ дҪҺеӨҙдёҖ笑пјҡвҖңе®ғеҸҳдәҶ пјҢ дҪҶе®ғиҝҳеңЁ гҖӮ еҸӘиҰҒзӨҫдјҡиҝҳиҝҷж · пјҢ жҖ»жңүдәәйңҖиҰҒе®ғ гҖӮ вҖқ
2019е№ҙ пјҢ еҪ“зәӘеҪ•зүҮгҖҠжқҖ马зү№ пјҢ жҲ‘зҲұдҪ гҖӢдёҠжҳ ж—¶ пјҢ еҪјж—¶24еІҒзҡ„зҪ—зҰҸе…ҙеҸҲдёҖж¬ЎеҮәзҺ°еңЁе…¬дј—и§ҶйҮҺдёӯ гҖӮ
дёҺд№ӢеүҚдёҚеҗҢ пјҢ иҝҷж¬Ўзҡ„е…іжіЁ пјҢ дёҚеҶҚжҳҜи®ҪеҲәдёҺеҳІз¬‘ пјҢ иҖҢжҳҜеӨҡдәҶдәӣиҝҹжқҘзҡ„зҗҶи§ЈдёҺе…ұжғ… гҖӮ
еҪұзүҮжІЎжңүжө“еўЁйҮҚеҪ©зҡ„дҝ®йҘ° пјҢ д№ҹжІЎжңүж—ҒзҷҪи§ЈиҜ» пјҢ д»…з”Ёй•ңеӨҙи®°еҪ•жқҖ马зү№е®¶ж—ҸжҲҗе‘ҳзҡ„ж—Ҙеёё гҖӮ
зәӘеҪ•зүҮгҖҠжқҖ马зү№ пјҢ жҲ‘зҲұдҪ гҖӢжө·жҠҘ
еҪұзүҮзҡ„еҜјжј”жқҺдёҖеҮЎжӣҫеқҰиЁҖ пјҢ жӢҚж‘„зҡ„еҲқиЎ·еҫҲз®ҖеҚ•вҖ”вҖ”дёәиҝҷзҫӨдёҚиў«зңӢи§Ғзҡ„дәәз•ҷдёӢеҪұеғҸ гҖӮ
第дёҖж¬ЎзңӢеҲ°жқҖ马зү№з…§зүҮж—¶ пјҢ д»–зҡ„йңҮж’јжқҘжәҗдәҺиҝҷдәӣеӨёеј зҡ„еҪўиұЎпјҡйЎ¶зқҖвҖңи§Ҷи§үзі»вҖқеҸ‘еһӢзҡ„е°‘е№ҙ пјҢ еёҰзқҖиҮӘеҳІдёҺеј жү¬ пјҢ еғҸжҳҜеңЁдёҖзүҮиҚ’еҮүдёӯиҮӘе»әзҡ„зәӘеҝөзў‘ гҖӮ
жҳҜзҡ„ пјҢ иҚ’еҮү пјҢ зјәе°‘зҲұдёҺе…іжіЁзҡ„иҚ’еҮү пјҢ жІҰдёәз•ҷе®Ҳе„ҝз«Ҙзҡ„иҚ’еҮү пјҢ з”ҹиҖҢдёәдәәеӯӨзӢ¬иҗҪеҜһзҡ„иҚ’еҮү пјҢ иў«ж»ҡж»ҡеҗ‘еүҚзҡ„ж—¶д»ЈиҪҰиҪ®ж— жғ…жҠӣејғзҡ„иҚ’еҮүвҖҰвҖҰ
жқҺдёҖеҮЎеҜ№дё»жөҒж–ҮеҢ–жҠұжңүж·ұж·ұзҡ„иӯҰжғ• пјҢ д»–и§үеҫ—жқҖ马зү№зҡ„еҮәзҺ° пјҢ жҳҜеә•еұӮе№ҙиҪ»дәәеҜ№е®ЎзҫҺжқғзҡ„дёҖж¬Ўж— еЈ°еӨәжқғ гҖӮ
вҖңиҝҷдёҚжҳҜеұұеҜЁ пјҢ иҝҷжҳҜдёҖз§Қе®ЎзҫҺзҡ„иҮӘи§ү гҖӮ вҖқ
еңЁд»–зңјдёӯ пјҢ йӮЈдәӣдә”йўңе…ӯиүІзҡ„еӨҙеҸ‘е’Ңе»үд»·зҡ„йҮ‘еұһйҘ°е“Ғ пјҢ иғҢеҗҺи—ҸзқҖдёҖз§ҚеҜ№и§„еҲҷзҡ„дёҚеұ‘е’ҢжҠ—дәүзҡ„ж„Ҹе‘і гҖӮ
дёҖеёӯгҖҠжқҺдёҖеҮЎпјҡжҲ‘жӢҚдәҶжқҖ马зү№гҖӢ
дҪҶйҡҸзқҖжӢҚж‘„зҡ„ж·ұе…Ҙ пјҢ жқҺдёҖеҮЎеҜ№вҖңжқҖ马зү№вҖқзҡ„зҗҶи§ЈеҸ‘з”ҹдәҶеҸҳеҢ– гҖӮ
д»–жң¬д»ҘдёәиҮӘе·ұеңЁи®°еҪ•дёҖеңәвҖңе®ЎзҫҺйқ©е‘ҪвҖқ пјҢ еҚҙеҸ‘зҺ°жӣҙеӨҡзҡ„жҳҜдёҖз§Қж— еҘҲзҡ„иҮӘж•‘ гҖӮ
вҖңеҫҲеӨҡдәәеҸӘзңӢеҲ°дәҶжқҖ马зү№зҡ„зҢҺеҘҮеӨ–еҪў пјҢ жІЎзңӢеҲ°жқҖ马зү№зҡ„еҚ‘еҫ®дәәз”ҹ гҖӮ иҝҷе…¶е®һжҳҜдёҖзҫӨжңҖеҸҜжҖңзҡ„дәә пјҢ е°ұйӮЈд№ҲдёҖзӮ№зҡ„иә«дҪ“ж”№еҸҳ пјҢ 他们被и§Ҷдёәй„ҷи§Ҷй“ҫзҡ„жңҖеә•з«Ҝ......вҖқ
ж‘„еҲ¶еӣўйҳҹиҠұдәҶдёӨе№ҙж—¶й—ҙ пјҢ йҮҮи®ҝдәҶдёғеҚҒеӨҡдёӘжқҖ马зү№жҲҗе‘ҳ гҖӮ 他们зҡ„ж•…дәӢеҮ д№ҺеҰӮеҮәдёҖиҫҷпјҡеҮәз”ҹдәҺеҶңжқ‘жҲ–е°ҸеҺҝеҹҺ пјҢ е№ҙе°‘иҫҚеӯҰ пјҢ иҝӣе…ҘеҹҺеёӮе·ҘеҺӮжҲҗдёәжөҒж°ҙзәҝдёҠзҡ„вҖңиһәдёқй’үвҖқ гҖӮ
他们用еӨҙеҸ‘е®Јжі„еҺӢжҠ‘ пјҢ з”ЁиҮӘжӢҚиҜҒжҳҺеӯҳеңЁ гҖӮ
еҸҜжңҖз»Ҳ пјҢ иҝҳжҳҜеңЁз”ҹжҙ»зҡ„йҮҚеҺӢдёӢеҪ’дәҺжІүеҜӮ гҖӮ
зәӘеҪ•зүҮгҖҠжқҖ马зү№ пјҢ жҲ‘зҲұдҪ гҖӢ
дёҖдҪҚеҘіеӯ©жӣҫеңЁй•ңеӨҙеүҚиҜҙйҒ“пјҡвҖңжңүдәәзңӢеҲ°жҲ‘зҡ„еҘҮиЈ…ејӮжңҚе°ұйӘӮжҲ‘ пјҢ дҪҶд№ҹиҜҙжҳҺ他们иҝҳзңӢеҫ—и§ҒжҲ‘ гҖӮ вҖқ
з«–иө·зҡ„еӨҙеҸ‘ пјҢ жҳҜдёҖз§ҚеӯӨзӢ¬зҡ„дҝЎеҸ·еј№ пјҢ зӮёдёҚејҖеҗҢжғ… пјҢ еҚҙиғҪеј•жқҘзӣ®е…ү гҖӮ
жқҺдёҖеҮЎеҸ№йҒ“пјҡвҖң他们жҠҠжҹ“иүІзҡ„еӨҙеҸ‘еҪ“дҪңдҝЎеҝө пјҢ еҸӘиҰҒйўңиүІиҝҳеңЁ пјҢ е°ұеғҸжңүдәҶи¶…и¶ҠзңјеүҚзҡ„ж„Ҹд№ү гҖӮ вҖқ
иҝҷдәӣе№ҙиҪ»дәә пјҢ з”Ёиҷҡжһ„зҡ„дҝЎеҝөеҺ»жҠөжҠ—з©әзҷҪзҡ„зҺ°е®һ пјҢ з”ЁдёҖж¬Ўж¬ЎиЈ…жү®и§Ұж‘ёдёҖз§ҚйҒҘдёҚеҸҜеҸҠзҡ„еҝ«д№җ пјҢ д»ҝдҪӣеҸӘжңүиҝҷж · пјҢ жүҚиғҪиҜҒжҳҺиҮӘе·ұеӯҳеңЁиҝҮ гҖӮ
вҖңжүҖд»Ҙ пјҢ д»ҺжқҘжІЎжңүзІҫеҪ©зҡ„жқҖ马зү№ пјҢ еҸӘжңүз”ҹе‘ҪжһҒе…¶иҙ«д№Ҹзҡ„жқҖ马зү№ гҖӮ вҖқ
дёҖеёӯгҖҠжқҺдёҖеҮЎпјҡжҲ‘жӢҚдәҶжқҖ马зү№гҖӢ
2019е№ҙ пјҢ зәӘеҪ•зүҮдёҠжҳ пјҢ дҪҶдҪңдёәвҖңжқҖ马зү№ж•ҷзҲ¶вҖқзҡ„зҪ—зҰҸе…ҙеҚҙ并没жңүе®Ңж•ҙзңӢиҝҮгҖҠжқҖ马зү№ пјҢ жҲ‘зҲұдҪ гҖӢ гҖӮ
вҖңиҝҷе°ұеғҸеңЁзңӢжҲ‘иҮӘе·ұзҡ„з”ҹжҙ» пјҢ иҖҢжҲ‘зҹҘйҒ“жҲ‘зҡ„з”ҹжҙ»жҳҜд»Җд№Ҳж ·еӯҗ гҖӮ вҖқ
жҲ–и®ё пјҢ зҪ—зҰҸе…ҙеҜ№й•ңеӨҙжңүз§Қжң¬иғҪзҡ„жҠ—жӢ’пјӣжҲ–и®ё пјҢ еӣ дёәйӮЈеӨӘеғҸдёҖйқўй•ңеӯҗ пјҢ жҠҠд»–иҝҮеҺ»зҡ„иҷҡиҚЈдёҺжҢЈжүҺ пјҢ иөӨиЈёиЈёең°з…§дәҶеҮәжқҘ гҖӮ
д»–ж„ҝж„Ҹжүҝи®ӨжқҖ马зү№зҡ„йҷЁиҗҪ пјҢ д№ҹж—©ж—©жҳҺзҷҪ пјҢ жүҖжңүвҖң家ж—ҸвҖқзҡ„з»Ҳз»“ пјҢ е…¶е®һйғҪеҪ’з»“дәҺдёҖдёӘиҜҚпјҡз”ҹеӯҳ гҖӮ
еІҒжңҲеғҸжҠҠж— жғ…еҲ»еҲҖ пјҢ жҠҠд»–ж—§ж—Ҙзҡ„еҸ‘еһӢеүӘжҺү гҖӮ
зҺ°еҰӮд»Ҡ пјҢ 29еІҒзҡ„зҪ—зҰҸе…ҙе·Із»ҸдёҚеӨӘе…іжіЁеӨ–з•ҢеҜ№вҖңжқҖ马зү№вҖқзҡ„иҜ„д»·дәҶ гҖӮ
иҜ„д»·жҳҜд»Җд№Ҳпјҹ
дёҚиҝҮжҳҜи·ҜдәәиЎҢиө°ж—¶жҺ·еҮәзҡ„дёҖдёӘзңјзҘһ пјҢ ж“ҰиӮ©иҖҢиҝҮ пјҢ ж— еЈ°ж— жҒҜ гҖӮ
他笑зқҖиҜҙпјҡвҖңжқҖ马зү№зҡ„зІҫзҘһжІЎжңүжӯ» пјҢ е®ғеҸӘжҳҜжҚўдәҶдёҖз§ҚеҪўејҸ пјҢ з•ҷеңЁдәҶиҝҷдәӣжүӢиүәйҮҢ пјҢ д№ҹз•ҷеңЁдәҶйӮЈдәӣдәәзҡ„еҝғйҮҢ гҖӮ вҖқ
иҪ¬жҲҳиҮӘеӘ’дҪ“е№іеҸ°еҗҺ пјҢ зҪ—зҰҸе…ҙз»ҸеёёдјҡеҸ‘еёғзҡ„дёҖдәӣжқҖ马зү№еҸ‘еһӢзҹӯи§Ҷйў‘ пјҢ 收иҺ·еҮ зҷҫдёҮзҡ„ж’ӯж”ҫйҮҸ пјҢ 并з”ұжӯӨеёҰжқҘдёҖ笔丰еҺҡзҡ„收е…Ҙ гҖӮ
вҖңжҲ‘зҺ°еңЁж”¶е…ҘжқҘжәҗжҜ”иҫғе№ҝжіӣ пјҢ дё»иҰҒжҳҜзҹӯи§Ҷйў‘ пјҢ дёҖдёӘжңҲе·ҘдҪңдёӨеӨ© пјҢ е№іеқҮдёүдә”дёҮеҗ§ гҖӮ вҖқ
еҰӮд»Ҡ пјҢ иҝҮеҺ»зҡ„вҖңжқҖ马зү№ж•ҷзҲ¶вҖқжҲҗдәҶзҹӯи§Ҷйў‘е№іеҸ°дёҠзҡ„жҷ®йҖҡеҲӣдҪңиҖ… пјҢ з”ЁеүӘеҸ‘е’Ңй•ңеӨҙеЎ«иЎҘз”ҹжҙ» гҖӮ
еҪ“иў«й—®еҲ°жҳҜеҗҰжғіжҲҗдёәзІүдёқеҚғдёҮзҡ„вҖңеӨ§зҪ‘зәўвҖқ пјҢ е®һзҺ°жүҖи°“зҡ„вҖңиҙўеҜҢиҮӘз”ұвҖқж—¶ пјҢ зҪ—зҰҸе…ҙж‘Үж‘ҮеӨҙпјҡвҖңжҲ‘еңЁиҝҷдёӘең°ж–№гҖҒиҝҷдёӘеҢә пјҢ жҲ‘и®ӨдёәжҲ‘жҳҜиҙўеҜҢиҮӘз”ұзҡ„ гҖӮ вҖқ
зҪ—зҰҸе…ҙдёҚйңҖиҰҒиұӘиҪҰиұӘе®… пјҢ д№ҹдёҚзҫЎж…•йӮЈдәӣжңҲе…ҘзҷҫдёҮзҡ„зҪ‘зәў гҖӮ
еҜ№д»–жқҘиҜҙ пјҢ иҙўеҜҢиҮӘз”ұзҡ„ж„Ҹд№ү пјҢ жҳҜеңЁд»–зҡ„ж¶Ҳиҙ№и§ӮеҝөйҮҢ пјҢ вҖңз•…йҖҡж— йҳ»вҖқ пјҢ жҳҜиғҪз»ҷжҜҚдәІеҜ„дёҖ笔й’ұж—¶дёҚеҶҚзҫһ愧 гҖӮ
д»–иҜҙпјҡвҖңжҲ‘ж•Јжј«гҖҒжҮ’ж•Ј пјҢ дҪҶеҸҲиҮӘз”ұ гҖӮ вҖқ
еҸҜзҪ—зҰҸе…ҙеҝғйҮҢд№ҹеҫҲжё…жҘҡ пјҢ иҝҷз§ҚвҖңиҮӘз”ұвҖқ并дёҚж„Ҹе‘ізқҖдёҖеҠіж°ёйҖё гҖӮ
з»ҸиҝҮдәҶиҝҷд№ҲеӨҡдәӢ пјҢ д»–еқҰиҜҡпјҡвҖңжҲ‘жӣҙеғҸжҳҜдёӘжүӢиүәдәә пјҢ жҠҠж—¶й—ҙе’ҢзІҫеҠӣз”ЁеңЁжҲ‘ж“…й•ҝзҡ„дәӢжғ…дёҠ гҖӮ вҖқ
жҺЁиҚҗйҳ…иҜ»
- еӨ©жҙҘжқЁе®¶зҲ¶еӯҗзҡ„жӮІе“ҖпјҒжҠҠж•ҙдёӘзӣёеЈ°з•Ңзҡ„дәәеҫ—зҪӘе…үдәҶпјҢжҗһеҫ—иә«иҙҘеҗҚиЈӮпјҒ
- еҢ—дә¬иҝҷжҷҡпјҢжҹіеІ©зҡ„иғҢзңҹзҷҪпјҢзЁӢжҪҮи…°еҘҪз»ҶпјҢеј йӣЁз»®зҡ„и…ҝжңүзӮ№зҹӯ
- жқҺжҷЁй«ҳи°ғе®ҳе®Је–ңи®ҜпјҒеҲҶжүӢеҗҺеҸҳвҖңиҙҹеҝғжұүвҖқзҡ„д»–пјҢз»ҲдәҺж‘Ҷи„ұдәҶеӣ°еўғпјҒ
- еҚҺжҷЁе®ҮпјҢиў«з—ӣжү№пјҡдёҖдёӘдёҚз”·дёҚеҘіпјҢйқ й¬је“ӯзӢјеҡҺпјҢе“—дј—еҸ–е® зҡ„жүҖи°“жӯҢжҳҹ
- еҸ‘зҺ°жІЎпјҹжӣҫз»ҸйңёеұҸзҡ„вҖңеңЈиҜһеҝ«д№җвҖқпјҢд»Ҡе№ҙдёәе•Ҙй”ҖеЈ°еҢҝиҝ№дәҶпјҹ
- жқҺдёҖжЎҗпҪңиҝҷи…ҝпјҒиҝҷи…°пјҒй»„йҮ‘дёүеӣҙзңҹдёҚжҳҜеҗ№зҡ„
- еҲҳдәҰиҸІжқҺзҺ°з»§и®ёзәўиұҶгҖҒи°ўд№ӢйҒҘеҗҺеҶҚж¬ЎеҗҢжЎҶпјҢжҲ‘еҚҙиў«40еІҒзҡ„жңұзҸ жғҠиүідәҶ
- и…ҫи®ҜйҰ–ж’ӯпјҒж–°дёҖйғЁеҸӨеҒ¶еү§жқҘиўӯпјҢе®…ж–—+жқғи°ӢпјҢз»ҲдәҺжңүеғҸж ·зҡ„еҸӨиЈ…еү§дәҶ
- жҹіеІ©зҙ§иә«иЈҷйҖ еһӢпјҡйӯ…еҠӣз»Ҫж”ҫдёҺиғҢеҗҺзҡ„ж•…дәӢ
- жӣқ2025еӨ®и§ҶжҳҘжҷҡеҪ©жҺ’и·ҜйҖҸпјҒзңӢдәҶеңЁеңәжҳҺжҳҹеҗҺзҪ‘еҸӢе“ӯдәҶпјҡдёҚиҜҘжқҘзҡ„жқҘдәҶ